文章分類Article
公司名譽受損可以請求精神賠償金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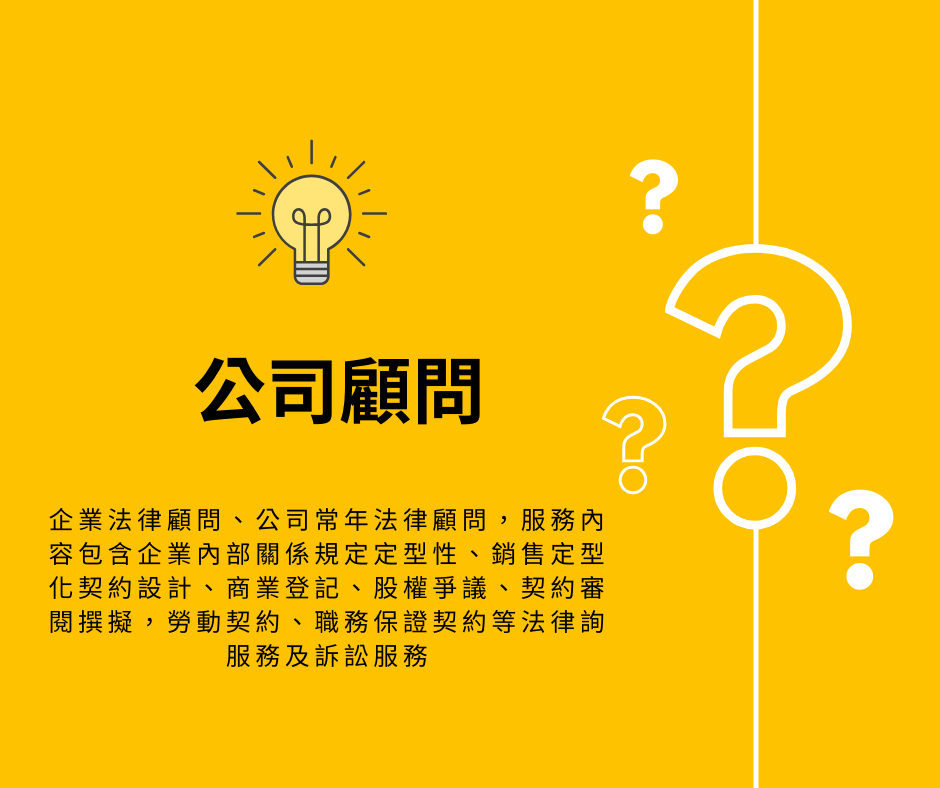
公司的名譽、信用遭受侵害時,是否可依民法第195條規定請求「非財產上損害賠償」?最高法院大法庭 112 年度台上大字第 544 號民事裁定
關於公司(法人)的名譽或信用,因為侵權行為或債務不履行遭受侵害時,公司是否可以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非財產上損害賠償?
對於這個司法實務上相當重要之問題探討,我們必須先來看民法第195條第1項前段究竟如何規定:「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又依民法第二章以下規定,民法中所稱之「人」乃包含「自然人」及「法人」;因此,若單就民法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所使用之文字以觀,條文用字係規範「人」,而並未將法人排除於本條規定當中,亦即似未限縮「自然人」始得主張。然而,另觀諸民法第26條規定:「法人於法令限制內,有享受權利負擔義務之能力。但專屬於自然人之權利義務,不在此限。」則關於法人的名譽或信用,因為侵權行為或債務不履行而遭受侵害時,究竟有無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非財產上損害賠償的權利,重點就在於,民法第195條第1項前段所規定,「名譽權、信用權受侵害時,得請求非財產上損害賠償之權利是否僅專屬於自然人方能享有」? 非財產上損害是否就等同於慰撫金?稱之為慰撫金者,是否就是指撫慰精神上痛苦之賠償金?法人並非自然人,無感受精神上痛苦之可能,那麼是否可請求慰撫金或非財產上損害賠償?
最高法院曾就此法律問題曾有正反兩面之見解
否定見解:法人並不會感受到精神上痛苦,自無請求慰撫金的可能。
公司係依法組織之法人,其名譽遭受損害,無精神上痛苦之可言,自無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精神慰藉金之餘地(參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599號判決、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434號判決)。
然而筆者認為,前開見解可進一步探討之處在於,所謂非財產上損害賠償是否即屬慰撫金?會有這樣的思考是因為民法第195條規定之並未使用「慰撫金」之文字,而是明文「雖非財產上損害,亦得請求相賠償相當之金額」,因此最高法院曾認為因法人並無精神上痛苦之可能,因此無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精神慰撫金之見解,是否確實符合民法第195條第1項之規範文義、規範目的,似有討論空間。
肯定見解:
按侵害法人之名譽,為對其社會上評價之侵害。又侵害法人之信用,為對其經濟上評價之侵害,是名譽權廣義言之,應包括信用權在內,故對法人商譽之侵害,倘足以毀損其名譽及營業信用,僅登報道歉是否即足以回復其商譽,自滋疑問。原審未遑詳加推求,僅以上訴人為法人,無精神上痛苦可言,即謂其不得請求被上訴人給付非財產上之損害,亦難謂洽(參最高法院90年度台上字第2109號判決)。
最高法院統一見解
對於以上最高法院曾有之正反兩面見解歧異情形,最高法院大法庭已於114年6月20日作成「最高法院 112 年度台上大字第 544 號 民事裁定」統一法律見解,並採取肯定之見解,詳細裁定理由如下:
人格權為受憲法第22條規定所保障之基本權利,並由立法者以民法等規定加以規範及落實。民法第18條第2項明定人格權受侵害時,以法律有特別規定者為限,得請求損害賠償或慰撫金,為人格權之一般性規定;至民法第19條、第194條、第195條第1項等規定,則將人格權予以個別化或具體化,為民法第18條第2項所指特別規定,且依民法第227條之1規定,於債務人因債務不履行,致債權人之人格權受侵害者,準用之。法人為依法律規定成立而具有權利能力(人格)的組織體,除法令或性質上之限制外,得享受權利負擔義務(民法第25條、第26條規定參照)。而民法第195條第1項所列舉之特別人格權,依其性質,有專屬於自然人者,如生命、身體、健康、自由、肖像等,法人固不得享有;但名譽、信用則非專屬於自然人,法人即得享有。又我國民法損害賠償制度,根據得否以金錢量化,將損害區分為財產上損害與非財產上損害,學說及本院先前裁判多認為民法第195條第1項前段之非財產上損害即為精神上痛苦,法人因無精神上痛苦,故不得請求非財產上損害之金錢賠償(以本院62年台上字第2806號原為判例為代表。下稱否定說),無非以該條立法理由記載「慰藉費」等語,及其立法時所參考之德國立法例及學說見解為據,符合當時社會實態,固無不妥。
然我國自民國18年制定民法第18條第2項規定至今,近百年未曾修正,88年修正民法第195條第1項規定至今,亦逾25年,於此期間,社會生活及交易型態、大眾媒體之面貌、訊息傳遞方式與速度,均與立法當時大不相同;另隨著法人經營型態國際化、多樣化,其組織規模日益增大,因名譽或信用遭侵害所受損害程度,無論規模或時間延續,均遠甚以往,甚至影響其設立目的之圓滿達成,對於法人名譽或信用之法律保障,更形重要。又民法第18條所繼受之瑞士法已修正其規定,許法人於一定要件下得請求非財產上損害之金錢賠償(瑞士債務法第49條),另如法國、日本、波蘭、歐盟及歐洲人權法院等判決,亦多予以肯認,已逐漸形成世界潮流。參以我國於88年增訂民法第514條之8規定,不論其文義(因可歸責於旅遊營業人之事由,致旅遊未依約定之旅程進行者,旅客就其時間之浪費,得按日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但其每日賠償金額,不得超過旅遊營業人所收旅遊費用總額每日平均之數額)或立法理由(現代社會重視旅遊休閒活動,旅遊時間之浪費,當認其為非財產上之損害。……如當事人對於賠償金額有爭議,由法院……,按實際上所浪費時間之長短及其他具體情事,斟酌決定之),均未以旅客受有精神上痛苦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成立要件,亦未限制其權利之讓與或繼承,足見我國立法者因應文明社會之發展,肯認時間浪費係有別於精神上痛苦之非財產上損害,應由旅遊營業人負賠償責任,顯已擴大非財產上損害之範圍,故非財產上損害不必再與精神上痛苦同義。至民法第18條第2項所稱慰撫金,名為慰撫,固專指以慰撫精神上痛苦為目的之金錢賠償而言;然該項所謂損害賠償,既未明定以財產上之損害賠償為限,解釋上自可包含慰撫金以外之其他非財產上損害賠償(含回復原狀與金錢賠償)在內,蓋非如此解釋,非財產上損害之回復原狀將失所依據。依上說明,難認依我國民法規定,法人就其人格權遭侵害所受之非財產上損害,概不得請求金錢賠償。
法人為依民法或其他法律規定所創設、並具有一定權利義務之組織體,在其設立目的之圓滿達成需求下,法律亦應賦與其完善之人格權保護。自然人之名譽或信用遭受侵害時,所受非財產上損害為因人性尊嚴受侵害所伴隨產生之精神上痛苦,即精神上之不圓滿,故應由行為人就被害人所受非財產上損害,負金錢賠償責任;而法人之名譽或信用遭受侵害時,因其實際上不具感性認知能力,與自然人有其本質上之差異,所受非財產上損害之內涵亦有不同,自應依其屬性,以受有對達成其設立目的有重大影響而無法以金錢量化之損害為限,准其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以兼顧人格權保障與防杜浮濫之立法意旨,並利遏止類此之侵害繼續發生。否定說未辨明時移世異,逕將民法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之非財產上之損害,限定於自然人之精神上痛苦,與立法者已擴大民法非財產上損害之範圍,及強化法人人格權保障之時代潮流不符,自非可採。
法人之名譽或信用,因侵權行為或債務不履行遭侵害所受之損害,原多屬得以金錢量化之財產上損害,此於被害人為營利法人時尤然;且縱令法人就其損害金額不能證明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法院亦應依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規定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至法人如另受有對達成其設立目的有重大影響而無法以金錢量化之損害,雖非不得請求金錢賠償,但仍應就該損害存在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此與被害人為自然人時,當然伴隨精神上痛苦,無待舉證之情形不同,附此敘明。
由以上最高法院大法庭裁定之裁定理由可知
名譽權、信用權並非專屬於自然人之人格權,名譽權、信用權對於法人而言,亦有相當之重要性,而應受保障,且此為憲法第22條所保障之人格權。
時至今日,依社會發展之情事以觀,非財產上損害不必再與精神上痛苦同義,亦即非財產上損害賠償之概念並非即屬撫慰精神上痛苦之慰撫金,因此不能再以法人並無可能感受精神上痛苦,因此否定法人之名譽、信用受侵害時得請求非財產上損害賠償之可能。
當法人之名譽、信用受侵害時,以受有對達成其設立目的有重大影響而無法以金錢量化之損害為限,而得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
如法人以能證明其名譽、信用確實受有侵害,且該損害已屬「達成其設立目的有重大影響而無法以金錢量化」者,則縱使法人就該損害具體金額不能證明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時,法院仍亦應依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規定酌定損害數額。
關於以上四點,看似以對於法人名譽、信用受侵害時得以請求非財產上損害賠償作成跨時代之肯定地、統一地見解;然而,後續法院實務運作究竟如何發展,關於所謂「受有對達成其設立目的有重大影響而無法以金錢量化之損害為限」應如何解釋?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規定於此類具體事件中應如何適用?都將會是法律上、訴訟上重要的攻防點,此相關爭議仍有賴法官、律師、專業法律人於訴訟實務中進一步思辯。因此,如有涉及法人名譽、信用受侵害之法律問題,仍建議應先與律師進一步諮詢、討論,以期能在最高法院大法庭作成本件裁定後,能夠在律師的專業協助下,始法人之名譽權、信用權於法院訴訟實務中獲得合理之伸張、維護。
>立即諮詢